著名翻译家杨德豫先生毕生追求的,正是《人生颂》里“年轻的心”对人生的壮丽想象,他沿着诗中昭示的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杨德豫(1928年—2013年),湖南长沙人,国学大师杨树达之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理事。1949年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随军南下。先后在一四二师、四十八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广州军区的报社任编辑。1958年下放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锻炼,后任高中语文和英语教员。1978年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主要译著有《朗费罗诗选》、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入《莎士比亚全集》)、《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英汉对照《华兹华斯抒情诗选》、英汉对照《拜伦抒情诗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等。2013年1月23日因病辞世,享年85岁。

接到杨德豫先生最后一个电话是在去年十二月中旬。那天,我跟随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在江苏常熟出差,手捧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再版“诗苑译林”(第一辑)样书向一群诗人征求意见。把酒言欢之际,手机响了。
按下通话键,耳边传来急促、略微高亢的声音:“傅伊同志,我是杨德豫。我接到你的信了,很感动⋯⋯”他说他目前健康状况很糟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虽然医生和女儿鼓励他,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反复地道歉,因为他在再版工作上帮不了我们。我嘱咐他安心养病,不要惦记着工作。酒桌上的人在等着我,我说得很简短,潜意识里认为以后还有机会与他通话吧。而且,他明显的情绪激动,令我不解。同行赞誉和读者推崇,对于他,并不陌生吧。
一月下旬参加杨先生追悼会后,在采访他的侄儿、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逢彬老师时,我无意间提起那最后一个电话和我的迷惑。我复述了信中几句话。 “跟《人生颂》的意思很像。”他缓缓地说。
《人生颂》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最著名的抒情诗之一,也是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此诗的各种译本中,杨德豫的译笔信而美,流传最广。
在聆听杨老亲人、故友和老同事怀着深情和无限遗憾述说往事的时候,在春节的鞭炮声中细读杨老唯一一部著述《追踪缪斯的踪影——谈英诗汉译及其他》的时候,在深夜反复品味他留下的那些精美绝伦的诗行的时候,我渐渐意识到,杨老毕生追求的,正是《人生颂》里“年轻的心”对人生的壮丽想象,他沿着诗中昭示的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在给他的那封信开头,我写道:
“在人生的战场上,您从来是一名勇士。”
世界是一片辽阔的战场,
人生是到处扎寨安营;
莫学那听人驱策的哑畜,
做一个威武善战的英雄!
(——引自《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宁为苍蝇不做哑畜
1956年秋天,广州军区《战士报》记者杨德豫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英语诗歌,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当时任职于广州军区司令部翻译科的汪飞白比他早一年开始翻译诗歌,同样遭到无理压制。这两个喜爱外国文学的年轻人对个人业余生活遭到组织干涉都不服气。杨德豫在反右前夕发表的文章《谁是谁非》,就是为汪飞白打抱不平而作。刚正不阿的杨德豫竟因好鸣不平而导致一生坎坷。
杨德豫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
大鸣大放的时候,地方鸣放很热烈,部队没有鸣放,想出气的人就觉得很憋气,要求“鸣放”。由我发起,报社的好几位同事联名写了一篇文章,要求“鸣放”。我们是部队报纸,广州军区领导压制“鸣放”。我把这个稿子投到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南方日报》,但上面有压力,这篇文章就没有在《南方日报》刊登。
(——引自《杨德豫的“左”“右”人生》:杨德豫,牟尼)
在这不久后召开的广州军区报刊座谈会上,他不惧权威,直言无忌。由于上述两条主要罪状,杨德豫被划为右派,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军籍,剥夺军衔,1958年6月被遣送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在洞庭湖畔当了20年“贼配军和苦役犯”。此间,与杨同期从广州军区下放到农场的300多名右派分子,近四分之一死于非正常原因。
1949年2月,长白师范学院学生张家骧在通州参加人民解放军,与来自清华大学的杨德豫住同一个炕上。当时,数以万计像他们这样的热血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为了解放南方和改变南方部队干部机构,弃学从戎随军南下。1958年6月,故人重逢竟然在农场新华书店,一见面就认出彼此,却不敢打招呼。沉重的政治包袱和压抑的现实环境使性格直爽的杨德豫变得内向,不想说话,甚至跟他一起出工的同伴很长时间都没听过他说话的声音。在那种处境下,杨德豫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看到政治乱象社会丑恶,他总是忍不住批评,“不说他就很痛苦”,张家骧说。
1966年7月,在农场中学教书的杨德豫和其他右派要求平反,农场领导不同意,杨德豫被揪斗游街,开除干籍和取消工资,再次下放生产队凭劳动工分计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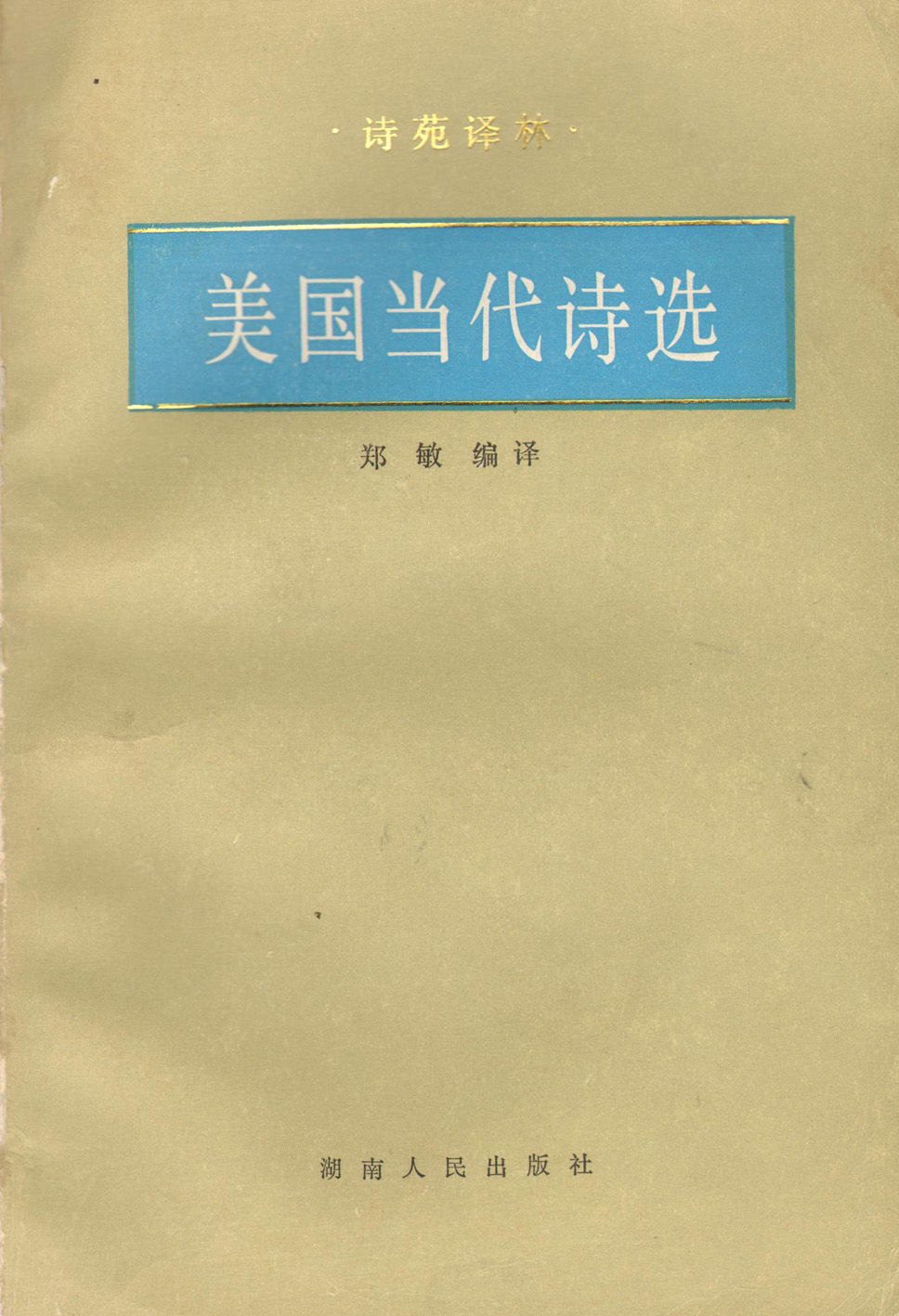
周殿芬是杨德豫在《战士报》的同事和好友洪长春的妻子。杨德豫从农场回长沙探亲时常到洪家做客,与其他遭难的右派好友聚会聊天,平反后也与洪家交往甚密。周记得,三中全会后中央为错划右派平反,同难者大多但求谋个公职找个“窝”。面对部队派来为他办理改正手续的老友,杨德豫毫无乞怜照顾之色,首先质问对方:“反右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
容貌清俊、仪态端庄的杨德豫自称 “从小就讨人厌”,“从小有点犯上作乱的思想,有点反骨”,为此吃尽苦头也不改本性。他在《墓志铭》中写道:“‘新时期’以来,仍然不思悔改,仍然我行我素,仍然粪土当今万户侯,仍然与时代主旋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注定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阎王。” 在纪念已故挚友、著名编辑杨坚的文章《旧交心为绝弦哀》中,杨德豫在赞美杨坚“绝不阿世,绝不‘紧跟’”的独立人格的同时,还是改不了早年在部队就为同事侧目的“刀笔吏”脾气,直言指斥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界“黄钟毁弃,铜臭熏天,斯文扫地”。
对自己“讨人厌”的命运,杨德豫处之泰然,还戏仿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墓志铭用于自己的墓志铭:
我活着也好,
死了也好,
我总是一只
讨厌的苍蝇。
这只嗡嗡叫的苍蝇,即使遭人厌恶被人痛击、驱赶,也绝不做“那听人驱策的哑畜”。
我们命定的目标和道路
不是享乐,也不是受苦;
而是行动,在每个明天
都超越今天,跨出新步。
(——引自《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善于劳动善于等待
汪飞白与杨德豫因译诗而相识相知,汪视杨为他最尊敬最信任的同道。杨德豫翻译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时缺乏英文原版参考资料,当时飞白任教于浙江大学,他从学校图书馆无人光顾的七楼阅览室里找到尘封多年的相关图书,不断借出来邮寄给杨。 杨在病危昏迷中还念叨飞白的名字。
“我们都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喜欢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哪里有压迫就扑向哪里,为了人性的解放而参加革命。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人文主义者,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飞白说。“当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碰壁,我们不约而同转向诗歌和翻译。除了因为我们大学都读外文系,喜爱外国文学,更希望通过译诗开个窗口,透进点海风,呼吸点新鲜空气,在当时政治高压下为人文精神的表达开辟一方小天地。”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无论遭遇何种挫折,经历何种苦难,杨德豫不改献身诗歌翻译的初衷,筚路蓝缕,不懈不止。曾和杨德豫同在农场劳动的好友白景高回忆,有时他晚上去找杨德豫聊天,看见杨德豫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看报或做翻译。湖区地势低平,夏天气温很高,蚊虫多,他就把双腿泡在装满水的桶子里,或者穿上雨靴。“他说:‘不这样的话,我的老本就丢光了。’”白景高回忆说。
曾任大通湖农场中学校长的陈守凡与杨德豫共事多年。杨德豫当时教语文课和英语课。他记得,除了上课和辅导学生,杨德豫很少跟其他人交流,总是把自己关在六七平米的宿舍里搞翻译。陈雄也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广州军区下放到大通湖农场的,1962年开始与杨德豫住得比较近,两人交往多起来。冬修水利时,每人每天要挑250担土,多数人从早上四点干到晚上九点,用茅草烧火照明,杨德豫这类身体弱、劳动技能差的队员常常要到十一点才能收工,回到工棚只有一桶已经泡过几十双脚、变成泥浆的热水。肖克勤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德豫是在1968年冬修水利期间,几个生产队的人住在一起。杨德豫跟谁也不说话,独自躺在地铺上,静静地看自费订阅的《光明日报》。

在每月工资6〜9元的条件下,杨德豫忍着辘辘饥肠,从牙缝里省下钱,托在长沙的周殿芬订阅当时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苏武在贝加尔湖畔与羊群为伴19年,常以草籽和雪充饥,绝不屈从于匈奴的威胁利诱,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两千年后洞庭湖畔风雨飘摇,结束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杨德豫急不可待地点亮煤油灯(肖克勤记得,他每月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镇上买煤油和鸡蛋;他只会煮鸡蛋改善生活),在阅读中“宽解这郁结的愁肠,驱除白昼的思虑”(《朗费罗诗选》:白昼已告终),文字和想象载着这个尘土满面的书生飞越漫漫黑暗。也许,某些夜晚,那个激情洋溢的异邦智者——他被打成右派前就已经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翻译《朗费罗诗选》——悄然来访,在他的心底热切呼唤:
那么,让我们起来干吧,
对任何命运要敢于担戴;
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追求,
要善于劳动,善于等待。
“诗苑译林”十年一剑
凭借深厚的知识储备,杨德豫在平反后很快胜任 “诗苑译林”的编纂工作。“诗苑译林”是五四以来我国第一套大型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 10年共出书51种,在读书界享有崇高威望,并于1991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据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的黎维新介绍,杨德豫虽不是名义上的丛书主编,但在工作中始终起到核心骨干的作用。除精心编校译稿之外,他凭借自己在国内翻译界和学术界的广泛人脉,策划了部分诗歌选题,并组织稿件;更为关键的是,他全面负责审稿工作,对译文质量严格把关,不仅保证了丛书整体质量,还对整个译文室起到业务指导的作用。“但八小时以内的业务都是审校别人的译稿,至于自己的翻译,纵然是应国家级出版社之约而译的,也被视为个人的‘私活’,只能利用零零碎碎的业余时间。”(——引自《杨德豫译诗集》后记)
杨德豫在《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后记里谈到该书的翻译情况:“回想起来,她(女儿杨小煜)读小学的六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译华兹华斯(只需扣除住院大半年,修改和增补《朗费罗诗选》大半年);她读中学的六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译柯尔律治(扣除住院一年多,修改《鲁克丽丝受辱记》大半年,以及出差几个月)。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除了译出《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外,十余年的精力和心血(在‘痴儿了却公家事’之后),差不多都倾注在这本书上了,比贾岛所说的‘十年磨一剑’犹有过之。”
杨德豫秉持英国诗人兼任译诗家雪莱的主张:译诗一定要用与原诗相同的形式来译,才算真正对得起读者。他遵循卞之琳的译诗原则,把英语格律诗译成白话格律诗,节奏和韵式都严格追步原诗。由于中西语言结构的差异,译诗实现形似是极其困难的。杨德豫殚精竭虑,锤字炼句,精雕细刻,以求译诗形神兼似。以《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为例。该书有译诗七十首,三千四百七十三行,韵式全部按照原诗,没有一行例外。此外,凡是原诗安排了行内韵的地方,译诗也都作了同样的安排。译诗“以顿代步”。全书三千四百七十三行中,至少有三千三百三十八行,即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诗行,译诗的顿数是与原诗的音步数完全一致的。对于另外一百三十五行(即不足百分之四的诗行)与原诗格律的差异,杨德豫逐一做了详细解释。尤其可贵的是,他还用图示明确说明译诗的脚韵安排与诗行起讫格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消除了读者由于部分译者误译而产生的对英诗诗行起讫格式的误解。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把杨德豫半个世纪以来所译莎士比亚一首长诗和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朗费罗四人的诗选结集付梓。杨德豫专门为《杨德豫译诗集》写了校勘记。他表示,译者一息尚存,译文的修改就没有止境,也不会有最后“定本”。他在病床上还在校订收入新版“诗苑译林”的《拜伦诗选》,通过邮件与编辑交流修改意见。
杨德豫对译诗艺术不倦不悔的追求取得了丰硕成果,也赢得了专家认可和读者好评。他翻译的拜伦诗选在大陆和台湾已刊行50万册以上,被老诗人、老翻译家卞之琳誉为“标志着我国译诗艺术的成熟”。他所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在首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彩虹奖的评奖中以全票名列第一。著名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屠岸先生曾评价杨德豫:“在现当代把英文诗翻译成中文诗的人中,他首屈一指。他翻译的量不多,面不广,但精益求精。他是译诗天才,也可称为译诗圣手。”
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
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
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
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
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
(——引自《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回想与杨德豫的多年交往,年近九旬的黎维新老人情难自禁数次落泪。杨德豫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时任社长的黎维新非常信任和倚重他,对他的家庭生活也颇多照顾。尽管如此,这位湖南出版系统的老领导心里还是有很多遗憾。“杨德豫一生有三个太少。”他说。一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太少,因错划右派受尽冤屈,不仅青春年华被耽误,健康也遭损害,一度生命难保,能够用于翻译的时间太少了,浪费了他的翻译天才。二是属于他的爱情太少,因为右派身份饱受歧视和孤独,51岁才结婚,没想到妻子长期患病,反而需要年老体弱的他照顾,吃饭、服药、睡觉,事事离不开他的看护。三是参加对外文化交流的机会太少。黎维新感叹,“我们本应该给他更多的创作自由,为国家文化和教育事业做贡献,不能因为地方主义和部门利益而限制甚至阻碍他的创作活动”。
著名出版家钟叔河的父亲与杨德豫的父亲杨树达先生曾同学于长沙时务学堂,两家素有往来。在钟叔河看来,杨德豫家学深厚,勤奋敬业,业务能力非常强,编辑的图书质量优良,生命力强,值得一印再印,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出版人才。“如果不是受到种种陈腐的观念的束缚,他本来可以过得更好些,比如住房条件更好点。比如,提供条件使他在离休后发挥余热,并给年轻编辑传授经验。我们纪念他,除了寄托哀思,就是希望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不公,不要再那样埋没人才,不能只考虑使用人才却不考虑给人才以合理的劳动报酬。”
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在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期间,直接领导、组织和参与了“诗苑译林”的选题策划工作。李冰封与经历相似的杨德豫相互理解,共同语言颇多。“杨德豫去世是中国知识界的损失。”他表情凝重,“文化、学术要发展,必须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必须允许讨论争执。”
杨德豫立身严谨,为人谦逊,陈雄说他“看起来冷漠,其实很重感情”。在老同事们的记忆里,他对人很友善,没有一点架子,“在社里从不显山露水,几乎无声无息”。了解杨德豫身世的人,无不对他心怀敬意和同情,对造成他人生不幸的魑魅魍魉充满愤恨。杨先生并没有因命运对他的不公而怨天尤人,以瘦弱的身躯默默承受着全部辛酸苦难。
在《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后记的末尾,杨德豫写道:
从1956年开始业余译诗,至今已将近四十年,其中有二十多年光阴无端虚掷,剩下的十几年,成果也寥寥可数。日忽忽其将暮,未免去意徊徨。记得华兹华斯说过:
我们只求自己的劳绩,有一些
能留存,起作用,效力于未来岁月;
(见《十四行组诗:达登河》中的《追思》一诗。)
倘能如此,于愿足矣,夫复何求!
杨先生一定不会失望,时间的沙上已经留下他的足迹,深深地。■







